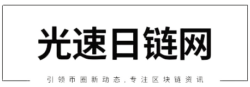[ad_1]
2022 年,印度最高法院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年内发生三次换岗。 掌舵的是三位首席大法官:NV Ramana,任期一年零 125 天; UU Lalit 的短期任期为 74 天; 现在是 DY Chandrachud,他的任期将持续到 2024 年 11 月。
用高级律师 Sanjay Hegde 的话说,Ramana 法官的任期可以是 总结 作为一个离开顶级球场的人,“比他发现它的时候稍微好一点……他的球场似乎准备好出击,但又害怕受伤”。
UU Lalit 法官的短暂任期将因大胆的决定而被人们铭记。 从在政治敏感案件中为活动家 Teesta Setalvad 和记者 Siddique Kappan 提供保释,到列出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案件,例如对经济较弱部分配额的宪法挑战,这得到了 解雇; 2016 年非货币化决定,这将得到 决定 1 月 2 日; 和《公民身份(修正案)法》。 正是在他任期内,最高法院实施了 直播 宪法席前的听证会。
CJI Chandrachud 现在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来对他热切期待的一切采取行动 谈到 ——一个透明的合议庭、一个包容的司法机构和一个对权力说真话的法庭。
2022 年也有重要的企业先例。
从澄清商品和服务税对海运的影响到在过渡信贷方面给予减免; 从为慈善机构带来税收透明度到对质押法作出裁决; 从对破产法判例造成潜在的干扰到使市场监管机构 SEBI 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等等都是最高法院在 2022 年做出的最高决定。
今年最大的税务案件之一是最高法院 验证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税务部门发出的 90,000 份重新评估通知。最高法院裁定,按照旧程序发出的通知将被视为按照修订后的规定发出。 尽管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税务部门的裁决,但仍有一些 一线希望也适用于纳税人:根据新程序,只有来自税务局的通知 最近三年 可以保留,而不是旧规则下的六年。 不久之后,中央直接税委员会发布了 指示 其官员以确保最高法院裁决适用方式的统一性。
在其关于直接税的第二项重大裁决中,最高法院 统治的 关于慈善机构何时可以申请免税。 要申请免税,教育机构应“仅”与教育或与教育相关的活动有关。 最高法院还规定了参与推进公共事业目标的法定公司、董事会、当局和委员会何时可以要求豁免的原则。
在间接税方面,最高法院对商品及服务税法的两个方面作出裁决。
第一个是过渡信贷。 对此,最高法院允许注册纳税人申请过渡性抵免。 这些是纳税人从以前的间接税制中结转的抵免额。 最高法院指示政府提供从 2022 年 9 月 1 日到 10 月 31 日的 60 天窗口,以允许纳税人提交新的过渡性信贷申请,并确保 GSTN 门户网站上没有技术故障。 最重要的是,这一判决的好处扩大到所有纳税人,而不仅仅是那些选择就此问题提起诉讼的人。 不久之后,GST 部门的操作指南出台,具体说明了索赔的方式 验证.
第二项判决对印度进口商来说是一个受欢迎的决定。 在此,最高法院裁定,中央政府不能根据运费保险合同对印度进口商的海运征收综合商品及服务税。 该裁决还引起了一些 不必要的混乱由于政府的错误的论点,围绕商品及服务税委员会的权力。
直到 7 月,债务和违约的证据足以让公司破产。 最高法院今年继续在组合中添加另一个“D”。 公司法法庭在提交破产申请时可以行使的自由裁量权。 该裁决是 重大偏离 NCLT 在考虑破产申请时的权力。 9月,最高法院驳回了对此事的复审申请。 Vidarbha 的判决很可能“听起来是 IBC 终结的开始,现在 NCLT 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包括调查违约的无数原因,并免除借款人偿还公共资金,破坏金融债权人的权利以及他们试图将资金带回系统”,高级倡导者 Ramji Srinivasan 当时告诉 BQ Prime。
然而,并非今年所有关于破产法的决定都令人惊讶。
在 ABG Shipyard 案中,最高法院 澄清 IBC 将优先于《海关法》,并且当清算程序开始时,海关不能根据《海关法》主张对货物的所有权并发出出售货物的通知。
在 Welspun Steel Resources Pvt. 的案件中,最高法院 等同于 清盘人的权力与债权人委员会的权力相同。 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机构在出售公司债务人资产时不能监督清算人方法的有效性。
在两个重大案件中,最高法院审查了 SEBI 提出内幕交易指控的方法。
它推翻了监管机构的决定 PC 首饰盒 并认为,如果不能证明拥有和分发未公开的价格敏感信息,则不能将交易模式单独用作内幕交易的证据。 SEBI 已寻求对该决定进行审查。
它还不同意 SEBI 在 阿比吉拉詹的案子 并为监管机构提出内幕交易指控设定了相当高的门槛。 最高法院裁定,内幕交易人员的获利动机是成功指控内幕交易的必要前提。 尽管该裁决是基于内幕交易的旧框架,但它可能会损害 SEBI 的“信息对等方法”。
在这种方法下,重点是内幕人士在交易公司证券时掌握的信息,而不是内幕人士实际上是否有意违法。 Umakanth Varottil,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副教授, 认为 最高法院的裁决可以通过明确内幕交易需要心理因素来对该理论产生更广泛的侵蚀。
[ad_2]
Source link